我们已经在别处强调过,支配一个时代位居首列的理念,虽然数量很少但是却很有力量,即使有时候他们只是纯粹的幻想。如今,做主导的理念是:教学能够让人发生重大改变,并且拥有某种特定结果而让人得到改善,甚至让人们能够平等。通过重复的事实,这个论点终于变成民主政体的最夯实的信条之一。对于这个论点如今也是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正如对待从前教会的那些教义一样,须得毕恭毕敬不得忤逆。
但是从这一点上来看,正如其他方面一样,对于民主理念,由经验和心理学分别给出的论据大相径庭。许多卓越的哲学家,如他们之中的郝伯特·塞宾斯,直截了当地指出,教学并没有在人的身上落实道德也没有让人更加幸福,它没有改变人的本能和传而来的激情;有时候没教好,反而弊大于利。统计学家最近也确认了这些观察,为我们指出:伴随着教学的普及,至少是某种教学的普及犯罪的行为增加了。社会最糟糕的敌人,就是安那其主义者,他们往往在学校的优等生中募集新成员;而在最近的工作中,我们杰出的法官阿多乐菲·古洛特先生做出了一份统计报告,计算出如今的罪犯中,有文化和没文化的比例是3000比1000。在50年中发生过的犯罪行为,在10万居民中的227件增加到了552件,增加了133%。他的那些同僚们也注意到,增加的犯罪活动尤其出现在年轻的人群中。正如我们所知,如今的学校是免费和义务制的,取代了缴费制。
当然并不是说,让人们都不要去支持教育普及,以为教学无法得到非常实用的实践结果。如果教学方向正确,就算不能提高道德,至少也发展了专业才能。不幸的是,拉丁系的人民,把自己的教学系统建立在荒天下之大谬的原则上,尤其是这25年以来!尽管一些最杰出的精英已经洞察到了问题,但是他们却可悲地一错再。我在自己的许多文章中都指出①:我们当下的教育,是把大部分受教育的人变成了社会的敌人,为糟糕至极的社会主义募集了大批信徒。
这种教育最危险的地方一用“拉丁范儿”一词来形容太合适不过了一是在心理学的基础上构建了这个错误,以为通过用心学习,手把手地指导,就能发展出智慧。从此,人们尽最大的努力这样学习。于是,从小学入学到博士毕业拿到学位,甚至到中学、大学教师资格会考,年轻人仅仅只是用心学习了课本,毫无自己的判断力与积极创造的精神,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在这方面训练过。对人而言,教学就是背诵和服从。“学习课程,用心记住语法、理论基础者大纲,不断重复,认真模仿”,这就是前任公共教育部长,于勒西蒙先生写下的,“一个滑稽的教育,就是用尽所有努力,只是为了心悦诚服地信奉师长永远绝对正确。这样只能贬低我们,让我们变得无能。”
如果这种教育仅仅只是没什么用处,人们也只是同情那些不幸的孩子,觉得孩子们在小学中该学的东西没学到,反而整天都在学什么克洛泰尔子嗣的谱系,奥斯特拉西亚和纽斯特利亚,或者生物课上的动物学分类。但是这其实出现了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这些带给孩子们的是令他们对自己诞生的地方产生强烈的厌恶情绪,并且产生强烈的欲望想要摆脱这一切。工人不想继续做工人,农民不想继续当农民。以及新生的资产阶级只知道让自己的儿女别尝试其他方式的人生,老老实实待在国家职能部门就职,领国家薪水就够了。这不是让人学会为自己的人生做准备,而是通过学校教给孩子们去为了成为公共职能部门的公务员做准备。由此而来的教育成果就是他们既不懂得为人处世,也无需展现任何积极创造的智慧火花。于是在社会最底层,创造出一大批不满自己的运的无产阶级队伍,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时刻准备着暴动;而处于较高社会阶层又怎样呢?我们轻佻浅薄的资产阶级,既多疑又容易轻信痴迷地自信身处福利国家之中,却又不断地批指责政府,把自己的过错和一无是处强加给政府,指责政府没有进行官方介入。
国家体制造就了大批拿文凭的毕业生。却仅仅只雇佣了他们中的一小撮人,这就造成了其他那些人失业。由此当然会出现,前者丰衣足食,后者反目成仇。从上到下,在这社会等级的金字塔中从简单的职工到教职人员或省长,一大群毕业人员至今仍纠缠于职场。批发商却很难找到一个代理人愿意去殖民地做工作,而成千上万的候选人,却在竞争办公室岗位,哪怕是办公室里最不重要的岗位。塞纳省进行了统计,仅小学男女教师就有2万人无业,然而他们却鄙视耕地和车间!反而向国家求助生活①。补贴下发的人数存在限制于是不满的人群必然越来越庞大。这些人时刻准备着发动一切形式的革命,这其中某些人就会成为首领,追求某些目标。有了知识却找不到工作,这种模式肯定会造就反叛者。
如今要扭转局面,显然已经为时太晚。唯有经验能告诉我们犯了什么错,它是我们最生动的老师。只有积累到足够庞大的经验,才能证明我们填鸭式的背书和可怜的会考,替换掉们是多么有必要!然后通过专业方向明确的技术教学指导——即所谓职业教育,重新引领年轻的人们奔向耕地、车间或者殖民地企业—而不像今天这样,不惜代价地想要逃离。
但凡有见识、头脑清晰的人,都在呼吁职业教育,这正是我们的父辈从前接受的教育,如今却引导着人民的意志、创造性以及企业的精神。留得住职业教育,才懂得号令天下。伟大的思想家泰纳先生,在他字字珠玑的文章中,我引用了一些最基础的部分,清晰地呈现出,我们从前的教育差不多就是当今英国或者美国的教育,并且在拉丁系统和盎格鲁一撒克逊系统之间,存在一个引人注目的平行对照,两种方式带来的结果一目了然。
也许在极端必要的条件下,人们会欣然接纳我们经典教育的所有弊病,就算它只是造成许多人失去社会地位并且心存不满,表面上接受了那么多知识,背起书来滚瓜烂熟无懈可击,总该提升了智慧吧!真的提高了?当然没有!判断力、创造力、经验、性格…这些人生中能够成功的条件,都不是书本里给出的。书籍作为参考就是有益的词典,但是如果把内容长篇大论地填进脑子里,则完全无用。
如何彻底解放传统教育,让职业教育能够在智慧的领域中发展泰纳先生用他的远见卓识告诉我们:
如同植物萌芽生长,理念仅在自然和正常的环境下形成。这都是无数的感觉印记,年轻人整日在车间、矿场、法庭、教室、工地、医院……所有场景中,接受到不计其数的深刻印象。他们观察着工具、材料以及操作,到场的客户、工友、任务作业,活儿干的是好是坏,是花钱多的还是有利可图的这一切都是来自眼睛、耳朵手感甚至嗅觉的独特感知,这小小的感知不知不觉地聚精会神并默默地烂熟于心,这些行为对他的暗示沉淀到一定程度,迟早会发生化学变化,形成新的产物,出现更加简洁、经济的改进,这就是发明创造。从这些珍贵的实践接触中,能够领会并必不可少的元素,这正是法国的年轻人被剥夺的元素,恰恰还是在他们拥有最好光阴的年纪;在七、八年时间中,他被囚禁在学校里,远离了直观的经验与个人经验。然而,原本就应该是这些经验为他奠定这些活生生事物的确的概念,以及各种各样与人打交道的方法。
至少十之八九的人在浪费他们的时间和他们的精力,如此一来好些年时光就这么浪费掉了,然而这他们生命中最高效、最重要甚至有着决定人生的几年。我们计算一下,参加考试的人群中,大约一半或者三分之二的人会落选一然后那些被录取的人终于大学毕业,获得合格证书与文凭,这些人中仍有一半或者三分之二的人疲于奔命。对他们的苛求太多了,要求他们某一天坐到椅子上,前面搁着一张桌子,两个小时的时间,要像人类知识的活字典一样回答各种科学问题;实际上,他们在这两小时中,或者差不多一整天,的确是一本活字典;但是一个月后,他们就差不多忘光了。他们不能再忍受新的考试。他们获取的知识繁多也太沉重,于是不断地从脑海中滑脱,并且他们不学习新的知识。他们心智的活力已经退化,充盈的元气也已经枯竭;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往往行将就木。循规蹈矩,结婚,逆来顺受…在这个圆圈中打转,无限循环,把自己囚禁在办公室的牢笼里;他把自己填得满满的,一切都是那么正确,绝不越雷池一步。这样是一般平均水平的收益,当然了,收益和支出完全不对等。然而在英国和美国,却和1789年以前的法国一样,人们的就业方式与现在相反,所获得的回报是对等的,甚至更优厚。
接着,这位著名的史学家呈现出不同于我们体系的那些盎格鲁-撒克逊人。他们并不拥有像我们这样数量庞大的专业学校。他们的教学并非依靠书本传授,而是通过实事。例如,工程师从车间里培养而不是在校园。这就使得每个人都能够精准地企及到自己能力容许的智慧程度。如果不能进一步发展,他还能当工或者工人。如果具备足够的才干,那就可以做工程师。对于社会这是更加民主、也更加有用的方式—比起把一个独立个体的全部人生,都押在18-20岁所遭遇的一场会考的几个小时里。
“在医院、矿场和工厂中,以及在建筑师、在法律人士的事务所里,被录取的学徒们都非常年轻,开始他的学徒期和实习,类似我们国家事务所里的文员或者工作室里的院的艺徒。作为入门准备,学徒工们要先学习一些普通而粗浅的课程,以便于建立好一个框架,来承载今后观察的内容。根据自己理解力的程度,往往一些技术性质的课程,需要占用他实习以外的暇时间,这样做才能逐步地作为日常经验积累。在同等体制下,相信了自己的实践操作能力并且进步,这样做提高了门生的才能,并且为他的今后工作需求的方向就做出相应的特定调整。英国和美国这种方式,让年轻人很快就懂得了学以致用。从25岁开始或者更早,如果设备条件和资金他都不缺乏,那么他不仅是一名熟练工,更可能成为自主创业的金业家;不仅能成为一个齿轮,更是一台发动机在法国,颠倒的方式已经占据上风,而每一代人,变得更加不知所谓,整个力量出现巨大的浪费。”
并且这位伟大的哲学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我们拉丁体系的教育和生活不相符。
“教学机构的三个阶梯——孩子、青少年以及青年人,坐在教室里通过书本学习理论知识,不但持久长而且学生们处于超载状态,还要考试、升年级、拿文凭和学位证书仅仅这些就已经够繁重了,然而更糟糕的是方式,通过寄宿人为训练和填鸭式灌输这是反自然和反社会的体制,用于实践学徒期来得太晚。如此疲于奔命地学习,根本没有考虑今后怎么,成年了怎么办,就让他们履行职责,对现实世界抽象且缺乏认知,年轻人很快面临失败利碰壁。应该在这之前,就应该让他们接触社会环境,让他们愿意接纳事实,为自己想要守护的东西去战斗、坚忍不拔——这些都得要提前准备,武装他们,使之训练有素,变得能够承受这一切。这是必要的准备,获取这个能力比其他一切都更加重要,精力、意志以及见识从而坚忍不拔,我们的学校却没有教。全都搞反了!我们的教育使得他们离这种能力相距甚远,甚至让他们在未来人生关键的条件中丧失了拼搏的资格。因此,当年人进入社会在实践的领域迈出第一步的时候,将痛苦地面临一系列失败甚至崩溃;他们跌得遍体鳞伤,长时间四处碰壁,有些人就破罐子破摔了。这是个严酷而危险的考验。道德和心智的平衡为此改变,并且短时间内难以恢复。幻灭来得如此突兀,却又那么彻底;失望是如此巨大,挫折感却又如此强烈。”①
在以上的内容中,我们远离了群体的心理学吗?当然没有。如果我们想要明白这些理念和信仰,是如何做到今天萌发明日开花,就应该知道其具备怎样的土壤。对于一个国家的年轻人给予怎样的教育,就能够预料这个国家有朝一日成为什么样子。对当代人所获得的教育来看,前途灰暗。一部分而言,教学和教育能够改或者改变群体的灵魂所以必须指出,当下的体系如何对这些进行育,以及那些漠不关心的中立人群,是怎样逐渐地变成心存不满的庞大队伍,时刻准备着服从于乌托邦分子和演说家的一切暗示。而这对于学校来说,今天造就的那些不满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将酝酿着拉丁系民族没落的下一时刻。


 相关文章
相关文章
 精彩导读
精彩导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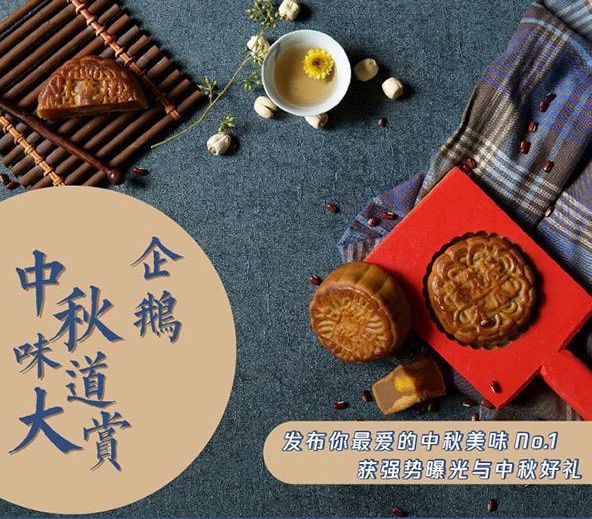
 热门资讯
热门资讯 关注我们
关注我们
